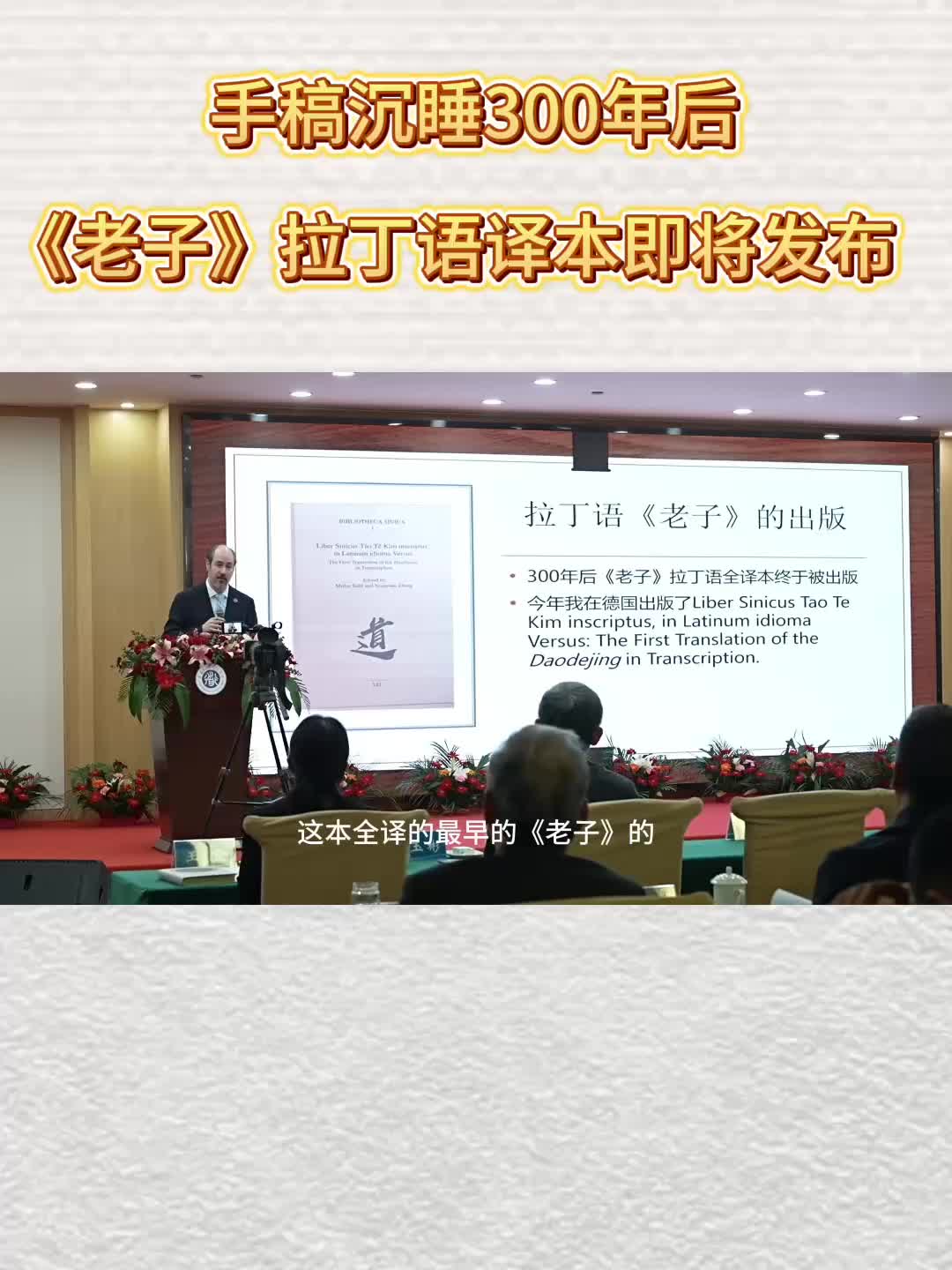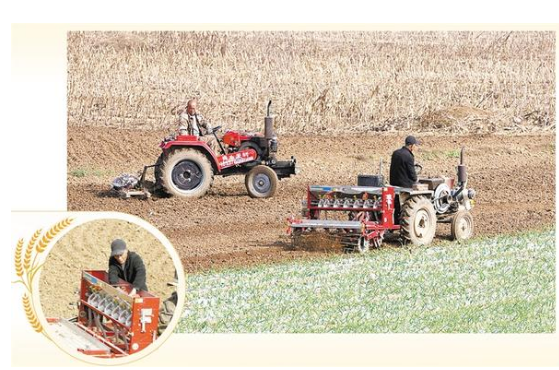李琰的文化苦旅與精神守望
黃亮
在嶺南文化的星空下,有這樣一位獨特的學者——他既是執筆論道的藝術評論家,又是身著“白襯衣”的高級警官;既是高校講堂上傳道授業的教授,又是博物館中策劃展覽的館長。李琰,這個名字背后,是一段從豫東平原到嶺南大地的文化苦旅,是一種在多重身份中堅守初心的精神守望。
1966年,李琰出生在豫東沈丘縣一個書香之家。這片被黃河文明深深浸潤的中原厚土,賦予了他骨子里的沉靜、堅韌和豐厚的文化底蘊。父親是他人生路上的第一盞明燈,那個用高玉寶“我要讀書”的故事啟蒙他的知識分子,在他1987年從淮南師專畢業到界首陶廟鄉中學任教后,又送給他一句終生受用的話:“人要站著活,書要站著教。”這句樸素的箴言,蘊含著中原文化中“寧折不彎”的風骨與“立德立言”的擔當,成為李琰此后數十年人生與學術生涯的精神底色。
站在鄉村中學的講臺上,李琰反復咀嚼著父親的教誨。“站著教”不僅是身體姿態,更是精神立場——不屈服于環境的艱苦,不妥協于現實的困頓,不隨波逐流于世俗的功利。這種“站著”的姿態、這份源自中原大地的淳厚與剛健,成為他后來所有選擇的內在驅動力。
1991年,李琰做出了人生中的重要抉擇——南下廣州,考入廣州美術學院攻讀中國美術史論碩士研究生。從中原到嶺南,從厚土到熱土,從教學一線到學術殿堂,這一跨越不僅僅是地理空間的轉換,更是文化語境與精神視野的拓展。在廣州美術學院這座藝術殿堂里,李琰深受嶺南畫派“折衷中西、融匯古今”革新精神的熏陶,更從楊之光先生“先學做人,再事丹青”的教誨中領悟到藝術與人格的統一。這句箴言與父親“站著活”的家訓,一南一北、一藝一道,在他心中產生了深刻的共鳴,共同塑造了他的學術品格與人生追求。
在碩士導師陳少豐先生的悉心指導下,李琰在廣州美術學院期間展現出非凡的學術潛力,連續發表多篇美術史論研究文章,在學術圈初露鋒芒。導師嚴謹的治學方法和開闊的學術視野,為李琰后來的學術道路奠定了堅實基礎。
然而,1994年研究生畢業后,李琰的職業選擇令人意外——他并沒有留在美術院校或研究機構,而是到廣東法制報刊社工作,成為一名司法宣傳工作者。從純粹的美術理論研究到法制媒體的實務操作,這一轉變看似突兀,實則暗合了李琰內心對“站著活”的更深理解——真正的思想者,不應囿于象牙塔,而應扎根更廣闊的土壤。這或許也是他中原基因中“經世致用”情懷的一種現實投射。
在廣東法制報刊社,李琰從記者、編輯做到經營總經理,身份的多元為他提供了觀察社會的多重視角。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從未放棄對美術史論的鉆研,《畫行天下——太行山》《宋元官私書畫鑒藏研究》等專著論文的出版,以及聯合編撰多冊高校美育教材,見證了他對學術初心的堅守。這種跨界生存的能力,已然成為他獨特的思想特質。
人生的軌跡再次轉折,李琰調至廣東司法警官職業學院任教,承擔美育和大學語文課程。這一次,他正式成為了一名光榮的人民警察,被授予三級警監警銜。警察與學者,這兩個在常人眼中矛盾的身份,在李琰身上達成了奇妙的統一。
身著警服的李琰站在講臺上,向未來的司法守衛者傳授美的理念、文學的力量,這本身就是一幅極具象征意義的畫面。他用自己的存在證明:法律的剛性秩序與藝術的感性認知并非對立,而是共同構筑完整人格的兩個維度。在紀律嚴明的警官學院推廣美育,不僅需要專業知識,更需要將兩種文化融合的智慧。
2015年,始終保持求學進取精神的李琰,跟隨中國藝術研究院顧森教授攻讀美術學博士研究生。顧森教授嚴謹的治學態度、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對學問的敬畏之心,深深影響著李琰。在顧森教授的指導下,李琰的學術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研究方法更加系統規范,學術視野更加開闊深邃。
李琰的“站著”姿態,在文化推廣領域同樣鮮明。作為廣東省美術評論學會會長、廣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他積極推動嶺南美術的學術研究與公共傳播;作為高劍父紀念館館長,他以公益之心守護著嶺南畫派的宗祠。這些工作雖然占據了他大量的時間,但他樂此不疲,因為在完成警官學院教學任務的同時推廣嶺南優秀文化,正是他踐行“站著活”的又一體現——在有限的條件下拓展無限的文化可能。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李琰策劃的“回家展”以其獨特的文化感召力,匯聚了來自11個國家和地區的華人畫家回到廣州,以藝術為紐帶,共同書寫對故土的情感與記憶。這一展覽不僅成為海外華人藝術界的熱門話題,更以文化的向心力贏得廣泛贊譽,彰顯了嶺南文化跨越地域的深遠影響力。
2018年9月,他發起并出資,在仲愷農業工程學院何香凝藝術設計學院等高校設立了以獎優助困為宗旨的“高劍父美術教育獎”。李琰在談及設立該獎的初衷時表示:“高劍父先生是嶺南美術精神的重要代表,他創辦的春睡畫院是其教育精神的重要載體,作為嶺南美術后學,我們有責任和義務將其精神傳承與發揚光大。”
翻閱李琰的著作,《高劍父研究文集》《李琰美術學文集》《美術經典中的共和國史》等,我們能從中感受到他學術視野的寬廣與深邃。這些豐碩的成果,不是書齋中的孤芳自賞,而是與時代對話的思想結晶。他策劃的諸多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學術活動與藝術展覽,更是將學術思考轉化為公共文化產品的實踐。
從豫東平原到珠江兩岸,從鄉村教師到警院教授,從司法工作者到美術評論家,李琰的人生軌跡如同一幅多層次的水墨長卷,每一筆都蘊含著對“站著”精神的詮釋。在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當代知識分子的一種可能——不固守單一專業領域,而是在多重社會角色中保持思想的獨立與批判;不沉溺于純粹理論建構,而是在理論與實踐的交匯處尋找思想的生長點。
父親“站著活”的家訓、楊之光“先學做人”的藝術哲學、陳少豐與顧森兩位恩師嚴謹的治學精神,這些滋養如同不同的溪流,匯同中原文化厚土所賦予的深沉與堅韌,共同匯成了李琰獨特的思想江河。而他發起并推動的“高劍父美術教育獎”,以及策劃的“回家展”等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正是這些精神資源在公共領域的生動展現——它們不僅是對貧困學子的經濟資助、對優秀學子的精神鼓勵,或是對海外華人藝術家的情感召喚,更是一種文化精神的傳遞。通過幫助一個個具體的、有血有肉的生命“站著”追求藝術理想,讓嶺南畫派的家國情懷與藝術精神,與中原士人的文化擔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交融、延續和光大。他的人生歷程證明,真正的學問最終要指向人格的完善,而完善的人格又必然反哺學問的深度,最高境界的“站著”,是家國精神。
“站著”的人、“站著”的思想,正是李琰給予我們這個時代最寶貴的精神啟示。他那從父親那里繼承而來、從中原厚土汲取力量并在人生路上不斷豐富的“站著”哲學,提醒著我們:真正有價值的人生,是在任何環境中都能保持精神的挺拔;真正有力量的思考,是在各種誘惑前都能守護思想的尊嚴。
嶺南的風依然潤澤,李琰依然繼續著他的文化苦旅與精神守望。他的故事告訴我們:人生的豐富不在于角色的多寡,而在于每個角色都能活出統一的精神高度;思想的深度不在于專業的壁壘,而在于不同領域間能建立起意義的橋梁。
這或許就是李琰——一位始終“站著”的學者。